(通讯员:梁浩榆)2022年12月17日9:30—11:3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希贤人文大讲堂·海外名家系列讲座”第十四讲“科学革命、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自然哲学与现代性的起源”通过Zoom会议的方式在线上举行。本次受邀的主讲者是牛津大学阿奎那研究所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特聘兼职教授、国际知名中世纪哲学专家和科学史家威廉·卡洛尔(William E. Carroll)。本次讲座由王成军老师主持,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近70名研究生,以及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Carroll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我们将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理解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事件,这也标志着以数学和实验方法为主要特点的现代科学逐渐兴起。但同时我们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论断,也即现代科学的兴起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及其中世纪继承者(如托马斯·阿奎那)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的拒斥。Carroll教授将会通过分析指出,当代流行的关于现代性和科学的基本假设往往会阻止我们仔细审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式的世界观,从而得到了“我们必须要在现代科学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传统当中做出选择”的论断,而这种推导过程和论断并非是充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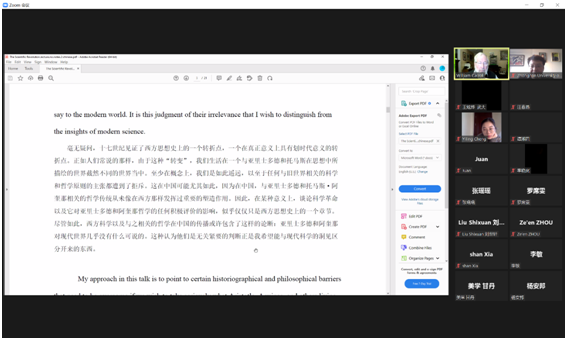
首先,Carroll教授引入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科学革命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一宏大叙事认为,科学革命不仅颠覆了中世纪的科学权威,也颠覆了古代世界的科学权威,它以经院哲学的衰落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倾圮而告终,从而宏大地耸峙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真正起源。其他流行的对科学革命的解释观点,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将科学革命定位于1277年对亚里士多德的各种命题发起谴责的运动;亚历山德尔·科耶(Alexandre Koyré)借助于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变迁来阐释科学革等,或多或少都表明了“科学革命是对亚里士多德科学的颠覆和摒弃”这一观点。
紧接着,Carroll教授从“科学革命的宏大叙事”入手对科学革命进行分析,他指出,尽管这个宏大叙事有许多枝节,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牛顿的惯性定律上,也即“每个物体都保持静止状态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除非施加在其之上的力迫使其改变这种状态。”而根据这一解释,牛顿的惯性定律与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任何运动都是由另一个运动引起的”和“一个物体的持续运动需要一个持续的动力因”的原理相矛盾,也就意味着如果牛顿是正确的,那么亚里士多德一定是错误的。此外,惯性定律也推翻了阿奎那的“第一条路”的论证(从运动到不动的推动者的论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中,物体的直线匀速运动都可以用惯性定律来解释,也即物体自身先前的运动并不需要任何其他动因。诸多证据表明,当代流行的解释倾向于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史上的一次彻底断裂,并且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都足以证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即除非受到外部运动的作用,任何事物都不会运动”是错误的。
但Carroll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转向惯性定律并稍加详细地考察它,我们就能够去辩驳那种认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牛顿科学之间根本不相容的论点,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到惯性定律是数学物理学中的一个原理而并非是一种自然法则。一方面牛顿的惯性定律是一个理想化的准数学概念,是数学推理模式的结果。在阐明惯性定律之前,牛顿给出了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的定义,他假设了“空气阻力不断减小直至零”这一情况下的抛射体运动。在这个讨论中,牛顿从一般经验的世界出发,去想象运动的极限情况,也即在这种情况下,抛射体将永远持续运动下去。而这里的极限概念来源于数学上的极限概念,换言之,惯性定律是在求极限的数学物理方法中推导出来的推论。另一方面,牛顿的惯性定律关涉到对任何物理性因果关系的抽象。牛顿认为,当我们在研究物体时,并不是就其是一种被赋有可感性质的物理实体而言的,而仅仅是就其是有空间延展的、可移动的、不可透视的东西而言的,也即惯性定律将物体简单地看作是缺乏本性的三维实在。但在我们生活的宇宙中,并不存在着任何缺乏本性(自然)的“三维实在”(“光溜溜的物体”),也没有永远进行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因而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不可能是一条“自然法则”。只有当我们设想惯性定律是一种自然法则,而不仅仅是数学物理学中的一个原理时,我们才会遇到如何处理它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关系这一难题。因此,我们并不能够简单认为牛顿的科学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理的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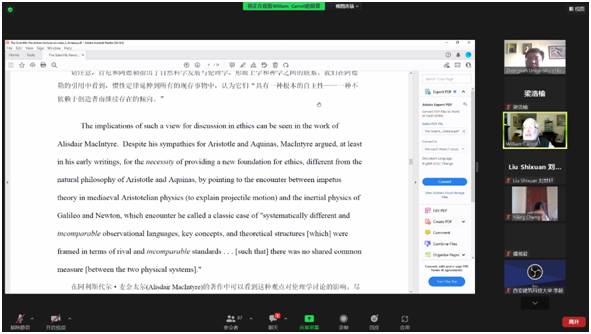
Carroll教授强调,将数学运用于运动研究必然涉及一个抽象的世界,而这个抽象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但也并不等同于自然世界。例如,牛顿清楚地知道,当他把“质量(mass)”定义为“物质的量(the quantity of matter)”,把“动量(momentum)”定义为“运动的量(quantity of motion)”时,他是在数学物理学的领域中进行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与其说牛顿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理的拒斥,不如说是对数学物理学这门科学的极大扩展和完善,而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 阿奎那的传统中,“物理学”或自然哲学是一门比各种经验科学更普遍的自然科学,它涉及到与时间的本性、变化的本性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相关的宽泛问题,也包含了所有个别自然科学的结论。
随后,Carroll教授将关注点从惯性定律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上。他指出:数学研究那些存在于可感物质中的维度和数量,但这些维度和数量可以脱离可感物质而被我们的理智所认识和理解数学和自然科学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以及认识对象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数学为自然世界所提供的解释并不如物理学所提供的解释更深刻,而数学也不能为自然科学提供科学探究的真正原则,因此,自然科学有与其自身相适宜的自治权。尽管对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来说,数学和物理学是自治的、有明显区分的科学,但一个人仍可以将数学原理运用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这种运用既没有出现在数学科学中,也没有出现在物理学中,而是形成了些融合科学:介于我们今天所称的“纯粹”数学和更普遍的自然科学之间的那些知识类型。但将数学原理运用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中永远不能够替代物理科学,因为物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完全现实性的物理实体。数学原理虽然适用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却不能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因和真实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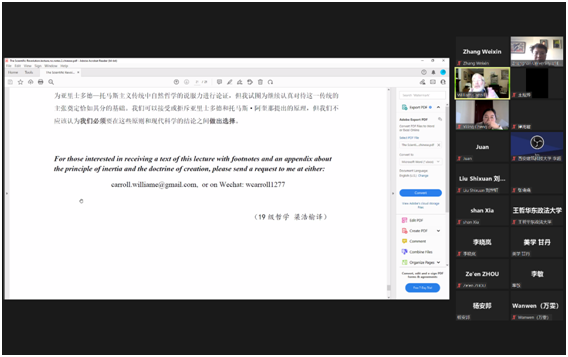
最后,Carroll教授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给出了他对于科学革命的理解。在他看来,科学革命中一些最伟大的成就发生在数学物理学中,也即发生在介于数学和物理学的那门科学之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是物理学领域的发展,与其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理的拒斥,不如说其标志着我们在理解如何将数学运用于物理实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今的科学历史之中的一种根本的连续性。这样一种关于科学革命的看法使我们摆脱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我们必须要在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之间做出选择。
在提问和交流环节,王成军老师为同学们补充和介绍了有关科学革命和“宏大叙事”相关解释的知识背景,同学们也踊跃地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数学物理学的对象和定义问题、惯性定律的推导原则问题等,Carroll教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耐心且详细的回答。在讲座的最后,Carroll教授再次表达了我院对他的邀请和对讲座的组织,并且希望今后能够前来武汉在线下与我院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